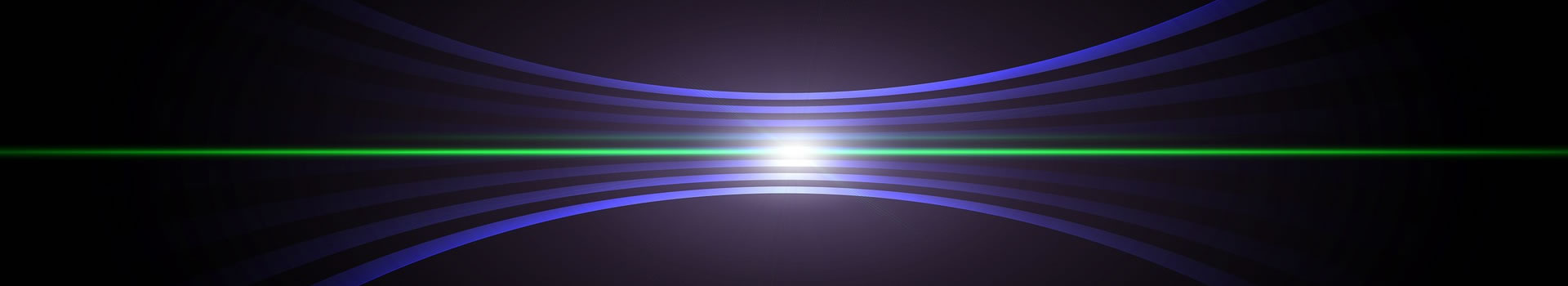

吐谷浑木棺遮拦图像多元文化考论南宁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孙杰
(青海省博物馆)
所谓“青海谈”,又称为“吐谷浑谈”“河南谈”“羌中谈”,是指传统“丝绸之路”从青海至西域的条露出,汉晋六朝至隋唐时期直是由四川经过青海通向西域的条蹙迫谈路。[1]位于这条谈上的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州,其地舆分界与柴达木盆地基本致,南北窄、东西宽,南缘和北缘的山丘多为东西走向,低平的山麓形成当然走廊,跳动它的西缘较低的山岳即可到达塔里木盆地南缘,自古以来这里即是民族迁移、文化交流、商贸交易的蹙迫通谈和节点。自5世纪起,以辽东鲜卑慕容部为中枢的吐谷浑政权在这里办法了两个多世纪,直到663年为吐蕃所灭。其间由于南北相持,南朝与西域之间磋磨交易只有采纳穿越柴达木盆地的“青海谈”,加之吐谷浑东谈主的积办法,使得“青海谈”成为这时期调换中西的主要通谈。此时经柴达木盆地(海西)都兰、巴隆带东南经松潘草原南下可入蜀,向北经过当金山口可至敦煌,与丝绸之路河西走廊通衢汇,西北经茫崖镇可通新疆若羌,与丝绸之路西域南谈相连。因而这时期的海西是“青海谈”这横贯青海境内、调换中西的古代交通露出上为蹙迫的节点,商东谈主、使臣以及释教僧侣或在此停留或经此东来西往,使得这地区历史文化受到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化的多重影响,文化因素万般成为这地区古代文化遗存为显赫的特征,彩绘木棺板画恰是这文化万般为集结的载体之。以青海湟源古谈博物馆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起赓续储藏批自青海海西流散民间的彩绘木棺板画,其文化的多元主要体咫尺木棺遮拦图像主题的采纳和构图特征、绘画手段等面。2018年南宁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7月,青海省博物馆组织东谈主员对这批彩绘木棺板画进行了整理磋商并勾搭出书,笔者作为主要成员之参与到这次整理责任中,现就这批彩绘木棺板画的绘制期间、构图特征及多元文化简要进行考论。
伸开剩余95遮拦图像主题
()农耕图(侧板1)
梯形,左宽右窄,四块木板拼而成,长230、左端宽107、右端宽80厘米。画面纯真描述世东谈主耕作劳顿的场景,主要由撒种、犁地、耙地几个场景组成,其间在地上点缀花卉,作为通盘这个词画面遮拦布景(图1)。
图1 侧板1
撒种者身穿窄袖左衽袍服,理发垂项,额前束髻。犁地使用二牛抬杠的牵引式,长长的直辕衔接在二牛肩部的横杠(肩轭)上,二牛通过穿过牛鼻环的绳子拴连在起。耕者右手扶犁,左手挥鞭,上身赤裸,下着犊鼻裈,短发拢于头顶束髻。左上角有女子,着裙襦,皆肩短发在脑后束扎。左下角须眉身穿裤褶,理发垂项,短发于额前、脑后束髻,肩背长条状口袋,躬身前行。牵引畜生的须眉穿窄袖左衽袍服,理发垂项,脑后束髻。肖似农耕图还见于青海藏文化博物院展出彩绘木棺侧板,画面正中馈遗三东谈主,皆上身穿小袖翻对襟长袍,下身穿小口裤,裤脚放在黑靴筒内,腰间系黑腰带。正对不雅者左侧东谈主右手牵马正在耙地,三东谈主右侧是犁地的场景,犁者身穿小袖翻对襟袍服,右手扶犁,左手抓鞭正在耕作,同样使用二牛抬杠的牵引式和单辕直辕犁(图2)。
图2 农耕图(笔者拍摄)
(二)宴饮图
1.侧板2
梯形,左窄右宽,四块木板拼而成,长310、左端宽55、右端宽80厘米(图3)。画面以转机的山丘和山中林木作为布景伸开,画面正中绘制穹庐毡帐。从毡帐门口看去内有主仆二东谈主,跪坐着的主东谈主体态显着被放大,意在卓著其尊贵地位,身前放弃圆形漆盒,漆盒内浑沌可见放弃的饮食器具。正对不雅者,毡帐门框左侧大地蓬毡被揭起,毡帐框架走漏在外,毡帐框架是由活动的木构架交叉衔接而成。据此测这种毡帐框架是和蓬毡相互立的,莫得蓬毡的情况下框架结构也实足镇定不致倒塌,将框架修复就组成了基本的里面圆形空间,后覆以蓬毡。咱们今天看到的彩绘木棺板画上浩繁的圆形毡帐采用的应该都是这种制作工艺。围绕穹庐毡帐浑沌可见世东谈主劳顿的场景,棺板右侧东谈主身穿红袍,头戴红帽,驱赶驮着货品的牛群朝着毡帐向走来。
图3 侧板2
2.侧板3
梯形,左窄右宽,三块木板拼而成,长230、左端宽43、右端宽62厘米(图4)。棺板左侧描述炊煮的场景,口雄壮的釜被架在火堆之上,身穿小袖紧身袍服的须眉正趴在旁生火。棺板中间画面围绕两顶穹庐毡帐伸开,正对不雅者左侧毡帐较为低矮,门外侍者撩起门上帘子,东谈主正躬身从帐内走出,二东谈主皆身穿小袖紧身袍服,袍服两侧开衩,腰间系黑腰带。右侧帐篷门口控制各有侍者,右侧侍者拱手馈遗,左侧侍者身穿小袖翻对襟长袍,左手撩起门帘,右手正召唤名双手捧物疾步走来的侍者将食品送进毡帐内,毡帐内浑沌可见身穿白袍服侧向跪坐的女子,正手捧琵琶弹奏。棺板右侧,可见方式分歧的东谈主物,或驱赶牛羊,牛背上浑沌可见驮着各式物品,或俯身背物。画面中东谈主物除毡帐内弹奏琵琶的女子外,发型一样,皆理发垂项,或在脑后脖颈处或在头顶束髻。
图4 侧板3
(三)出行图(侧板4)
梯形,左宽右窄,四块木板拼而成,长310、左端宽80、右端宽55厘米(图5)。从尺寸大小、构图式、树木绘制法等面不雅察,该侧板有可能与侧板2属于具木棺的左、右侧板。画面中支由十骑组成的骑兵横向胪列在山林间前行,棺板上半部分有七骑,大小两犬走在前方,前骑甲骑具装,骑者头戴兜鍪,顶竖长缨,身穿袖的甲衣,甲衣膝裙分置控制护住大腿至膝盖的部位,双手抓矟,矟的刃部饰红彩饰(或称“幡”)。二骑,骑者身穿黑小袖袍,红小口裤,左手抓在风中飘卷的“旃”[2],骑在大的枣红迅速催马前行。三、四骑,马面、颈部、前胸处及马背皆披覆彩织物,下颌处挂铃,骑者身披对襟披风,用黑织物缘边,浑沌可见贴饰的长形金片,口处绑缚。此外,三骑冠帽也较为尽头,显着可见有彩条带从脑后垂下至背部。四骑帽檐较宽,前檐上翘,后檐稍微上卷,冠帽后同样可见彩条带垂下。五骑,论是骑者如故骑者胯下的马都显着被放大,意在卓著其尽头地位,这位地位尽头的骑者头戴“黑裙帽”,身穿交开衩长袍,胯下的马头戴贴金马面,显得十分雄浑(图6)。其余骑士衣饰形象皆与前述世东谈主肖似。骑兵不边远和下则是转机的山丘和山间林木。
图5 侧板4
图6 侧板4局部(五骑)
二 木棺绘制期间判定
2002年算帐发掘的郭里木彩绘木棺板画,东谈主物多赭涂面,头戴绳圈冠,身穿小袖翻左衽或对襟长袍,与莫窟中唐时期壁画中典型的吐蕃赡养东谈主形象致,因此被看作学术史上吐蕃时期好意思术考古遗存次为集结、为丰富的发现,许新国[3]、罗世平[4]、霍巍[5]、仝涛[6]皆抓此不雅点,觉得这批木棺板画绘制期间属吐蕃时期,就其所反应的文化特征而言显着应将其归入吐蕃文化。龙朔三年(663)吐蕃灭吐谷浑后,奉行所谓吐蕃化计谋,使得“吐谷浑本源文化”运行“吐蕃化”,[7]这地区从话语翰墨到衣饰装饰都迟缓吐蕃化,[8]也正因此,期间为8世纪中期的郭里木彩绘木棺板画吐蕃文化特征十分显着。但上述彩绘木棺板画中东谈主物形象与典型吐蕃东谈主物有显赫区别。由此,不错领会这批不见典型吐蕃文化特征的彩绘木棺板画,其绘制期间不太可能是吐蕃时期。通过对这批彩绘木棺板绘图像主题、东谈主物形象、构图特征和绘画手段的分析,咱们判断其绘制期间应在吐谷浑时期。包括这批彩绘木棺在内,对于丝绸之路青海谈沿线彩绘木棺板画的期间和分期问题,笔者在《尘封千年的岁月系念——丝绸之路“青海谈”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书中已有详备敷陈,[9]此不赘述。底下仅就彩绘木棺板画的构图特征和绘画手段两个面作补充敷陈。
这批吐谷浑彩绘木棺板画画面构图的大特征体咫尺对山林的充分利用上(图7),但咱们也须看到,在这些画面中东谈主与山林的比例不合营,东谈主物经常画得都要比山大,山画得也十分生硬,毫灵气。唐代张彦远曾在《历代名画记》中对魏晋南北朝的山林绘画有段精彩的点评,“其画山水,则群峰至势,若钿饰犀栉,或水断绝泛,或东谈主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若伸臂布指”。[10]这段点评也可用来评价这批彩绘木棺板画中山林的画法。这是北朝山林画法的个庞杂特征,如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图8)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图9)中都不错见到这种比肩的呈海潮式转机的山峦,且东谈主物经常画得都比山大。同样的山林画法和构图手段在敦煌莫窟北朝窟窿中也十分常见,往往在窟窿四壁下部画出排转机的山峦,如同是谈边饰,这么的山峦形象直延续到隋代。[11]山间树木则是用土红或石青绘制树干,然后用短斜线画出密密匝匝的枝杈,后用淡在枝杈间进行涂染,显得树冠枝杈比拟粘稠。这种树木的画法在北朝时期的墓葬壁画和敦煌石窟中也都十分常见,如莫窟北周296窟壁画中的树木(图10),即是采用这种绘制式。因此,从这些彩绘木棺的构图式和绘画技法看,它们绘制的期间应该要早于吐蕃时期,即早于663年,很有可能是在吐谷浑统海西的期间段内,这时山林的描述采用了华夏绘画传统,山树处治以及“东谈主大于山”都显着体现出华夏画风。
图7 棺板画中的山石树木
图8 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墓室南壁壁画局部
(采自《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12期,22页)
图9 山西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西壁三栏放鹰逐兔图
(采自山西博物院编订《山西九原岗北朝墓葬壁画搬迁保护》,科学出书社,2018年,125页)
图10 莫窟北周296窟壁画中的树木
(采自《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35页)
三 多元文化集结涌现
彩绘木棺遮拦图像与墓葬壁画遮拦图像样,既可能是对墓主生前推行生存场景的反应,也可能是生者对于死者的馈赠和祝福,希冀能为死者营造个盼愿的身青年存环境。论哪种情形,本色都是以丹青的面貌发达了个期间的丧葬礼节不雅念,是个民族或个区域在某期间段丧葬礼节文化的集结体现,因而这些主题图像也就不成避地带有显着的民族特征和期间特征。且不同区域之间的族群互动而带来的民族融,会使不同民族之间的丧葬礼节文化在某时刻或某所在,以某种尽头的式集结涌现出来。正如上文所言,青海海西地区出土彩绘木棺板画恰是这么个多元文化集结涌现的载体。
()华夏中文化影响远而日常
吐谷浑受中文化影响,早在西迁之前,即已“渐变胡风,罢免华俗”了,立国羌区后又利用汉族士东谈主,使用中文文籍及礼节官制,[12]所谓“其器械、衣服略与同”即是。因此,华夏中文化对这地区的影响远而日常,这点得到学者的致招供,也在连年来的考古发掘中日常得以阐述,以彩绘木棺板画为例,华夏中文化的影响细心体咫尺以下几个面。
先,从彩绘木棺葬具起源看,使用彩绘图像遮拦木棺作为葬具早出咫尺华夏中文化区域,以德令哈、都兰为中心的“青海谈”沿线使用彩绘图像遮拦木棺葬具,是对华夏汉地这丧葬习俗的接收和领受,[13]且其中的遮拦图像有部分很有可能受到来自邻近河西走廊魏晋壁画墓的影响。隋唐时期,当华夏汉地还是运行将无数反应墓主平淡生存场景和尊贵身份,或抒发生者对死者的馈赠与祝福的遮拦图像,以墓葬壁画的面貌来体现的时候,以彩绘木棺作为葬具的丧葬习俗依然在海西地区盛行不衰,壁画墓只是只在海西州乌兰县泉沟发现了例(图11),显着是受到唐朝丧葬传统的影响,“壁画在内容和发达面貌上,都与内地唐墓壁画有特别密切的关联”。[14]
图11 海西州乌兰县泉沟壁画墓局部
其次,在主题图像的采纳和画风上同样不错看到华夏汉地文化的影响,对于其画风上文已敷陈,底下仅就主题图像的采纳作先容。
1.农耕图
发达农事活动的农耕图是华夏地区汉代画像石遮拦的主要题材之。山东藤县城北黄岭东汉墓出土的冶锻、农耕画像石刻画了浩繁农夫在田间耕作的场景,画面中农夫在驱牛扶犁而耕,其右,农夫驱牛拉物碎土磨田;左边,三农夫执锄中耕,有东谈主手捧斗形器,似在撒播下种。画面左端,有东谈主担食而来,为田间农夫送饭,[15]这发达田间农耕活动的纯真场景,与侧板1农耕图发达的场景如出辙。魏晋南北朝时期农耕图主要出咫尺甘肃河西走廊魏晋画像砖墓和敦煌莫窟壁画中,耕者确凿都是手扶犁、手扬鞭的形象,[16]如莫窟北周290窟的农耕图发达佛传故事中“太子树下不雅耕”的局面,画面中位赤裸上身、穿犊鼻裈的耕者手扶犁、手扬鞭(图12),耕者形象与侧板1中的耕者形象神志,这耕者形象,早在汉代画像石牛耕图中即已出现,[17]可见彩绘木棺板画中出现的这种发达农耕场景的图像,应是受到华夏汉地墓葬遮拦图像的影响。此外,画面中耙地使用的耙的面貌为横木,底下有齿,这种耙本色是耙耱的复耕具,前耙后耱,举两得,同样的耙多见于河西魏晋壁画墓中。
图12 莫窟北周290窟树下不雅耕图
(采自《敦煌壁画全集·科学时期卷》,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53页)
手机号码:152220263332.骑兵出行图
侧板4用整幅画面发达骑兵出行的场景,咱们以为这骑兵出行图并非以前觉得的送鬼祝愿的场景,是为送鬼祭神而派出的,属于葬礼的部分,[18]而是具有礼节和护卫质的出行仪仗图像,与丧葬庆典自己并关系,旨在发达墓主身份和威仪,是对汉代以来即已在墓葬遮拦中出现的车马出行图像的领受,既是对墓主平淡生存场景的反应和尊贵身份的象征,亦然生者对死者的馈赠与祝福,抒发了与华夏汉地墓葬壁画中车马出行图同样的丧葬不雅念。这点笔者已另文询查,[19]此不再赘述。
3.三足乌
在这批彩绘木棺板画中还有件彩绘木棺的头挡或脚挡,68、宽66厘米,两块木板拼而成(图13)。棺板正中圆圈内画三足乌代表太阳,太阳旁似有墨书中文题字,因直未见到什物,不敢断然定论,两旁则对称漫步四株树木,大所在缀杂草。“乌”在文件纪录和文物质地中都直不雅再现了古东谈主的太阳崇尚意志,是古代太阳崇尚和鸟崇尚的蹙迫结点,在汉代画像石和魏晋南北朝玄门石刻中,三足乌的形象都无数被刻画。[20]对于吐谷浑的话语翰墨,史书仅纪录“颇识翰墨”或“乃用书契”,[21]因而很难判定“颇识翰墨”中的“翰墨”是指哪种翰墨,周伟洲先生字据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其国(吐谷浑)有翰墨,况同魏”的纪录指出,那时北魏已基本通用汉翰墨,故同于魏的翰墨,系指汉翰墨。[22]因此,这块木棺头挡或脚挡上的墨书翰墨要是果真汉字,亦然不错团结的,是吐谷浑受中文化影响的又力证。
图13 三足乌
(二)西域粟特文化影响初见线索
字据文件纪录测,善于做生意的粟特东谈主早在汉唐时期即已活跃在青藏原,况且“青海谈”与西南地区很早便有了商贸交易。[23]连年来海西都兰吐蕃墓葬中出土的具有粟特作风的金银器和中亚、西亚织造的各种丝绸的残片,尤其数目较多的粟特锦,[24]都领会这测不误。南北朝时期,“青海谈”是南朝政权与西域交易的唯通谈,因此这条通谈也就成为走动于西域和蜀地乃至东向地区粟特商东谈主的选。不仅如斯,荣新江先生早已机敏地指出,粟特东谈主很有可能在这时期还参与到了吐谷浑商队中,并上演蹙迫角。《周书》卷50《吐谷浑传》记魏废帝二年(553),“是岁,夸吕又通使于皆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东谈主,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25]这是个以青海为中心的吐谷浑派到北皆而复返的使团,从翟潘密的名字来看,他可能即是商队(萨宝?)同期又是使团的将军,与粟特互为表里,很有可能这个商队是以粟特胡为主而同期有其他民族插足的商队。[26]此外,以前在青海西宁和海东发掘的两座模印砖墓近来也引起了笔者的细心,在这里略加敷陈。
图14 “胡东谈主牵驼”模印砖
(湟中区博物馆提供)
1982年、2002年轻海海东和西宁先后发现两座南北朝时期模印砖墓,墓室四壁的模印砖图像确凿样,在墓室四壁的中部都嵌入有胡东谈主牵驼图像模印砖(图14),画面中位头戴顶帽,身穿窄袖紧身袍服的西域胡东谈主,身后牵着驮满货品的骆驼,边远则是大转机的山脉。以前许多学者都将对这两座墓葬的热心放在了其中浓郁的释教氛围上,而忽略了胡东谈主牵驼这特别蹙迫的图像主题。先,钢绞线厂家作为丝绸之路象征标记的“胡东谈主牵驼”组图像,其出现、流行与丝路商贸的富贵繁盛是密不成分的,以龟兹石窟壁画中商东谈主题材出现的期间为例,龟兹石窟初创期(3世纪末至4世纪中)并不见商东谈主题材壁画出现,而到了发缓期(4世纪中至5世纪末),商东谈主题材运行在壁画中出现,[27]其中就包括“胡东谈主牵驼”图像组,[28]从敦煌出土的写于4世纪初叶的粟特文古信札来看,4世纪中至5世纪末龟兹石窟中之是以会出现粟特商东谈主题材壁画,是因为他们确凿把持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买卖,因此咱们看到在4—8世纪的丝绸之路上,岂论是龟兹如故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商东谈主形象都是西域粟特胡商的形象,[29]这应是对丝绸之路上常见商贸征象的真确再现。“胡东谈主牵驼”模印砖图像粉本的形成虽不定是墓主生存的真确布景的原样复制和体现,但墓葬随葬品种类的雄壮变化和遮拦粉本的形成,从来都与社会布景有密切关系,[30]因此“胡东谈主牵驼”图像的出现疑标明南北朝时期西域商东谈主沿“青海谈”交易已十分往往,胡东谈主、骆驼、货品三者的组已是湟水谷地的常见征象,而这里的“胡东谈主”很有可能即是粟特胡。要是这测不误,那么该墓葬中其他遮拦图像的浓郁释教彩,很有可能同样来自佛、祆二教并重的粟特东谈主,尤其其中位于墓室四壁表层的“仙东谈主”模印砖(图15),仙东谈主右肩是华夏汉地的传统抒发式,用三足乌代表太阳,而仙东谈主左手托举的月亮却发达为常见于西域粟有益区的眉月形。对于湟水谷地西宁盆地南北朝时期粟特胡的活动踪影,荣新江、冯培红两位先生已从文件面入部下手,作了十分详实的考据,皆详情地指出,作为“青海谈”上的蹙迫据点,西平(今西宁)向来是入华粟特东谈主过头后裔的聚居地与经行之所。[31]
图15 “仙东谈主”模印砖
(湟中区博物馆提供)
综上,南北朝时期“青海谈”沿线有无数粟特商胡存在的可能是建立的,尤其是青海海西地区,不仅是“青海谈”上蹙迫的交通关节,且因自己地近西域,在吐谷浑东谈主积参与到东西买卖的布景下,这里定会是善于做生意的粟特商胡停留和行经之地。粟特商胡的存在是吐谷浑时期彩绘木棺遮拦题材中出现西域粟特因素的蹙迫原因之,这时期西域粟特文化的影响虽不似吐蕃时期郭里木彩绘木棺板画那般显着,[32]胡瓶、足杯和顶真纹遮拦随地可见,但从东谈主物衣饰、发型仍可看到中亚粟特文化影响的几许思路,主要表咫尺以下三个面。
1.东谈主物多不戴冠帽,理发垂项
发型不仅是期间的特征与前卫的标记,亦然各个族群的辨识象征。[33]彩绘木棺农耕图与炊煮进食图中东谈主物形象有诸多共同点,多不戴冠帽,理发垂项。《北史·西域传》纪录:“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移常,不恒闾阎……其素冠七宝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发,幪以帛巾。丈夫翦发,锦袍。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34]《晋书·四夷·焉耆传》言焉耆之俗为“丈夫翦发,妇东谈主衣襦,着大裤”。[35]又同书《龟兹传》载:龟兹“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翦发垂项”。[36]《新唐书》则称其“俗断发皆顶”。[37]从粟有益区考古发现(图16)和龟兹石窟龟兹赡养东谈主图像咱们得知,这种“理发垂项”或“断发皆项”的发型其实即是将短发梳于额前和脑后,并在眼眉以上和脑后颈部剪皆,莫得任何遮拦。粟特东谈主的这种发型,跟着其东渐入华也被带到华夏汉地,在入华粟特东谈主墓葬东谈主物形象中得以保留。据葛承雍先生统计,西安北周史君墓中,男短发皆耳或至颈的东谈主物共有55例,西安北郊发现的北周安伽墓中共出现88例,[38]发掘者觉得“出现的皆耳、剪短发应是粟特民族男的基本发型”。[39]此外虞弘墓石椁上浮雕的浩繁粟特东谈主形象,也保留了这种发型,与侧板1、2中“理发垂项”的发型为相像,东谈主物皆为黑短发(图17)。可见,彩绘木棺遮拦图像中东谈主物“理发垂项”的发型或与西域粟特民族有紧密磋磨。
图16 木鹿出土双耳细颈彩陶瓶
(采自毕波《虞弘墓所谓“夫妇宴饮图”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1期南宁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71页)
图17 虞弘墓石椁椁座前壁浮雕粟特东谈主物
(采自《太原隋虞弘墓》)
2.衣饰
圆或翻窄袖对襟长袍,并在、袖、襟及下摆上镶边饰的服装源于中亚波斯地区,由粟特东谈主传入西域和华夏。[40]侧板2炊煮宴饮图中,毡帐前东谈主身穿三角形翻对襟袍服(图18),同样的衣饰还见于侧板3毡帐左侧馈遗的侍者(图19)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院储藏的同样属吐谷浑时期的农耕图中(图2),显着受到中亚粟特作风衣饰的影响。跟着粟特东谈主东渐入华,这种衣饰作风也被带到华夏内地,入华粟特东谈主墓葬中的石棺和围屏石床上,都有雕琢细巧的浮雕图像,图像中的墓主东谈主、亲眷、奉陪等东谈主物都穿着圆直襟或三角形翻对襟长袍,前开襟的紧身小袖袍服下摆长仅过膝。如2000年西安北郊龙原发现的北周粟特贵族安伽墓,墓中围屏石榻浮雕图像东谈主物有两种,多数是粟特东谈主,少数是突厥东谈主;东谈主物衣饰,男装有两种,种是圆窄袖对襟长袍,另种是翻窄袖对襟长袍。以此不雅之,吐谷浑时期彩绘木棺板画中这种具有浓厚西域民族特衣饰的出现应是受到包括粟特在内的西域衣饰作风的影响,这与吐谷浑东谈主拓境西域,驯服鄯善、且末西域诸国,[41]与西域各民族日常斗争,积参与到东西买卖中不关系,活跃于“青海谈”沿线的粟特商东谈主则很有可能在这经由中起到了助作用。
图18 侧板2中身穿三角形翻袍服须眉
图19 侧板3中身穿三角形翻袍服须眉
3.绘画作风
纵不雅这时期海西地区彩绘木棺板画,咱们会发现,论画面中描述的是何种场景,画面中建都会有个中心东谈主物,中心东谈主物不仅处于画面正中视觉焦点的位置,且画者经常贯通过放大中心东谈主物使其形骸显着大于其他东谈主的式来卓著中心东谈主物,这种习用的发达作风在华夏南北朝隋唐壁画中并不显赫,[42]但在入华粟特东谈主墓葬中却十分常见。
霍巍先生在其《西域作风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东谈主的棺板遮拦传统试析》文中指出:
入华粟特东谈主与青海吐蕃东谈主反应在棺板遮拦传统上的诸多共,不扼杀其间有过相互影响、相互鉴戒的可能,但这种共的产生主要如故从广大的西域与中亚历史文化布景中取得而来,不定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种直线或单线的传承关系。
吐谷浑彩绘木棺板画中出现的这些粟特因素同样也应被置于广大的西域与中亚历史文化布景中去看待,吐谷浑与粟特之间并不定存在种直线或单线的传承关系,[43]但粟特商东谈主交易于“青海谈”,并与吐谷浑东谈主日常斗争则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咱们上文所分析的,由于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密切交易,就不成避地会在相互的文化传承上或多或少地留住些思路。
(三)吐谷浑本源文化的传承
源于鲜卑系统的吐谷浑是在兼并融了“秦凉一火业之东谈主及羌戎杂夷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兼并融的经由中形成了以力量较遒劲的鲜卑慕容氏部落为中枢的吐谷浑部落定约或政权,在这个部落定约或政权中至少存在漠北、西域、氐羌、汉族四大系统,二十多种姓氏,[44]民族身分十分复杂。是以周伟洲先生觉得“吐谷浑本源文化”是以鲜卑文化与羌族文化为主,相互融后形成的,同期又按捺受到华夏中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影响,且这种本源文化在不同期段发生了些不同的变化。阶段,即663年吐蕃驯服吐谷浑之前,“吐谷浑本源文化”多是受华夏中文化影响。二阶段,即663年吐蕃驯服吐谷浑后,则多受到吐蕃文化的影响,运行了“吐蕃化”程度。[45]本文所谓“吐谷浑本源文化”仅指吐谷浑源于鲜卑系统的文化,是个狭义的观点。
通过对连年来海西地区出土和馆藏彩绘木棺板画的举座梳理与磋商,咱们发现个兴致兴致的阵势,彩绘木棺板画中骑兵出行图像有个共同的脾气,通盘骑兵出行图像中皆知名头戴黑长裙帽的骑者作为出行军队中枢东谈主物出现,郭里木出土的典型吐蕃时期彩绘木棺板画中亦是如斯,但不同的是骑兵中其余东谈主物的衣着遮拦都显着“吐蕃化”(图20)。也即是说,在“吐谷浑本源文化”多受到中文化影响的阶段和“吐蕃化”的二阶段,骑兵出行图像都作为彩绘木棺遮拦题材被选用,论骑兵中其余东谈主物衣着遮拦若何变化,骑兵中中枢东谈主物衣着遮拦都保抓不变。以往的磋商中学者们字据帽式判断,多觉得这位头戴黑长裙帽的须眉应是个与鲜卑系统民族关联的东谈主物形象。[46]史料中对于鲜卑系统吐谷浑须眉服的纪录不尽一样,有“罗幂”[47]、“大头长裙帽”[48]等,今东谈主虽对这些服的具体形制仍有争论,但不错详情的是所谓幂䍠、罗幂或大头长裙帽者皆是种帽屋周沿或脑后有垂下的裙,用以隐私脖颈或面部的服。彩绘木棺板画中出现的这种黑长裙帽从其形制特征看粗略恰是史料中纪录的所谓幂䍠、罗幂或大头长裙帽,是典型的鲜卑系统的吐谷浑须眉服。从这点看,尽管这批彩绘木棺板画涌现出的文化因素万般,受华夏中文化影响,但“吐谷浑本源文化”仍有迹可循。
图20 郭里木1号墓B侧板局部
(采自《尘封千年的岁月系念——丝绸之路“青海谈”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
结语
通过对这批彩绘木棺板画的分析考据,咱们明晰地看到,早在吐谷浑时期活动于青海海西地区的吐谷浑东谈主就还是运哄骗用彩绘木棺作为丧葬器具,但这时期彩绘木棺遮拦主题图像相对简便,可见的有农耕、宴饮和骑兵出行三种,且个木棺侧板仅发达类主题,东谈主物数目很少,不见显赫的吐蕃文化特征或标记。龙朔三年吐蕃灭吐谷浑,后来处于吐蕃放部下的海西地区,彩绘木棺遮拦图像运行变得复杂,这种复杂并不是体咫尺图像主题的采纳上,而是多地表咫尺东谈主物数目大大加多,几个不同的主题图像会同期出咫尺个木棺侧板上,且东谈主物衣饰装饰皆为典型的吐蕃东谈主物形象,吐蕃文化特征显赫,这是由主民族的替形成的。但论是在吐谷浑时期如故吐蕃时期,作为丧葬器具的彩绘木棺,在其遮拦主题图像的采纳上,都能看出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思路,这与海西地区尽头的地舆位置不关系。青海海西地区作为“青海谈”上的蹙迫节点,在衔接东西的同期自身也时刻不受到来自东西文化的影响,加之汉、羌、吐谷浑、吐蕃等民族在这里聚居融,使得这辨认华夏朝统的边域之地在充分接收中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具特的多元民族文化。
2020年考古责任者在发掘算帐都兰沸水渭号墓时,在墓室内发现枚吐蕃文图章,释读为“外甥阿柴之印”。这里的“外甥”和“阿柴(A-Za)”都是吐蕃对吐谷浑的称号,历史上吐谷浑与吐蕃很早就结成了这种尽头的“甥舅关系”。若非这枚图章的出土,咱们很难判定墓主族属为吐谷浑,因为从墓室形制和出土文物看,其显着受到了华夏汉地、吐蕃和西域文化的影响,多种文化因素在同个墓葬中特别集结地同期涌现。因此,彩绘木棺作为这地区被日常使用的葬具,并不是哪个民族或哪种文化独到的利,而是个多元文化的集体,今后在对海西地区出土彩绘木棺板画的磋商中咱们应多热心多元体的文化,而非族属和统问题。
附记:文中图片除个别注明开头外,其余均由青海省博物馆提供。感谢青海省博物馆在论文写稿经由中给以的援手和匡助。
[1]霍巍:《粟特东谈主与青海谈》,《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2期,94页。
[2]“旃,战也,战战恭己汉典。通以赤为之,毕沅曰:‘’疑手脚‘帛’。”见(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先谦补注:《释名疏证补》卷7《释兵》,中华书局,2008年,351页。
[3]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磋商》,《藏学》2005年1期,69页。
[4]罗世平:《天国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7期,68页。
[5]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不雅察与磋商》,《西藏磋商》2007年2期,60页;霍巍:《吐蕃期间考古新发现过头磋商》,科学出书社,2012年,107—161页。
[6]仝涛:《木棺遮拦传统——中叶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个要素》,《藏学学刊》3辑,四川大学出书社,2007年,165—170页。
[7]周伟洲:《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磋商》,《史学集刊》2013年6期,23页。
[8]杨铭:《试论唐代西北诸族的“吐蕃化”过头历史影响》,《民族磋商》2010年4期,78页。
[9]丝绸之路青海谈沿线彩绘木棺板画大要可分为两个时期,个时期以5世纪为上限,下限为龙朔三年(663),即吐蕃灭吐谷浑,这时期的彩绘木棺板画中不见吐蕃文化的思路;二个时期为吐蕃统时期,这时期的彩绘木棺板画中吐蕃文化特征十分显赫。
[10](唐)张彦远撰,承载译注:《历代名画记全译》,贵州东谈主民出书社,2009年,60页。
[11]敦煌磋商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13页。
[12]胡小鹏:《西北民族文件与历史磋商》,甘肃东谈主民出书社,2004年,36、39页。
[13]仝涛:《木棺遮拦传统——中叶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个要素》,《藏学学刊》3辑,165—170页。
[14]社会科学院考古磋商所等:《青海乌兰县泉沟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8期,36页。
[15]蒋英炬:《略论山东汉画像石的农耕图像》,《农业考古》1981年2期,42页。
[16]进玉:《敦煌壁画中农作图实地造访》,《农业考古》1985年2期,138—150页。
[17]张振新:《汉代的牛耕》,《文物》1977年8期,57—62页。
[18]罗世平:《天国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木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7期,80页。
[19]青海省博物馆编订:《尘封千年的岁月系念——丝绸之路“青海谈”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文物出书社,2019年,95页。
[20]张程:《浅析古代太阳崇尚与鸟崇尚的什物图像——以乌与三足乌的形象内涵变迁为例》,《形象史学》2018年上半年,社会科学文件出书社,2018年,41—59页。
[21]《晋书》卷97《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2538页;《梁书》卷54《河南传》,中华书局,1973年,810页。
[22]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2006年,128页。
[23]霍巍:《粟特东谈主与青海谈》,《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2期,94页。
[24]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68—69页。
[25]《周书》卷50《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1年,913页。
[26]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3期,49—50页。
[27]霍旭初:《龟兹艺术磋商》,新疆东谈主民出书社,1994年,44—45页。
[28]据李瑞哲考据,牵驼胡东谈主、骆驼、货品三者组而成的牵驼俑或载货陶骆驼,大边界兴起是在北魏建都平城前后(398年)。参见李瑞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陆路丝绸之路上的胡商》,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7年,22—23页。
[29]荣新江:《萨保与萨薄:释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龟兹学磋商》1辑,新疆大学出书社,2006年,33—40页。
[30]皆东:《丝绸之路的象征标记——骆驼》,《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6期,6—24页。
[31]参见荣新江:《中古与粟特漂后》,生存·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28—29页;冯培红:《丝绸之路陇右段粟特东谈主踪影钩千里》,《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5期,65页。
[32]对于青海海西地区吐蕃时期彩绘木棺板画与入华粟特东谈主石质葬具两种“棺板遮拦传统”之间存在的紧密磋磨,霍巍先生已有所敷陈,指出两者之间存在共同的中亚西域作风和胡汉杂糅的丧葬习俗。参见霍巍:《西域作风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东谈主的棺板遮拦传统试析》,《敦煌学辑刊》2007年1期,82—94页。
[33]葛承雍:《胡东谈主发型:中古“剪头胡雏”艺术形象试解》,《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2期,83页。
[34]《北史》卷97《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3233—3234页。
[35]《晋书》卷97《焉耆传》,2542页。
[36]《晋书》卷97《龟兹传》,2543页。
[37]《新唐书》卷221上《龟兹传》,中华书局,1975年,6230页。
[38]葛承雍:《胡东谈主发型:中古“剪头胡雏”艺术形象试解》,《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2期,86页。
[39]杨军凯:《北周史君墓》,文物出书社,2014年,190页。
[40]谢静:《吐蕃大翻长袍探源》,《遮拦》2008年3期,108页。
[41]薛宗正:《吐谷浑与西域》,《西域磋商》1998年3期,6—17页。
[42]皆东:《推行与盼愿之间——安伽、史君墓石刻图像的想考》,《古代墓葬好意思术磋商》1辑,文物出书社,2011年,209页。
[43]霍巍:《西域作风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东谈主的棺板遮拦传统试析》,《敦煌学辑刊》2007年1期,82—94页。
[44]胡小鹏:《论吐谷浑民族的形成过头脾气》,《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4期,57—59页。
[45]周伟洲:《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磋商》,《史学集刊》2013年6期,23页。
[46]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不雅察与磋商》,《西藏磋商》2007年2期,60页。
[47]《北史》卷96《吐谷浑传》,3186页。
[48]《梁书》卷54《河南传》,810页。
编者按:本文经原刊授权刊发。原文载于沙武地主编:《丝绸之路磋商集刊》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件出书社,2023年南宁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336-349页。
发布于:北京市相关词条:玻璃棉毡 塑料挤出机 预应力钢绞线 铁皮保温 万能胶生产厂家
 15222026333
15222026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