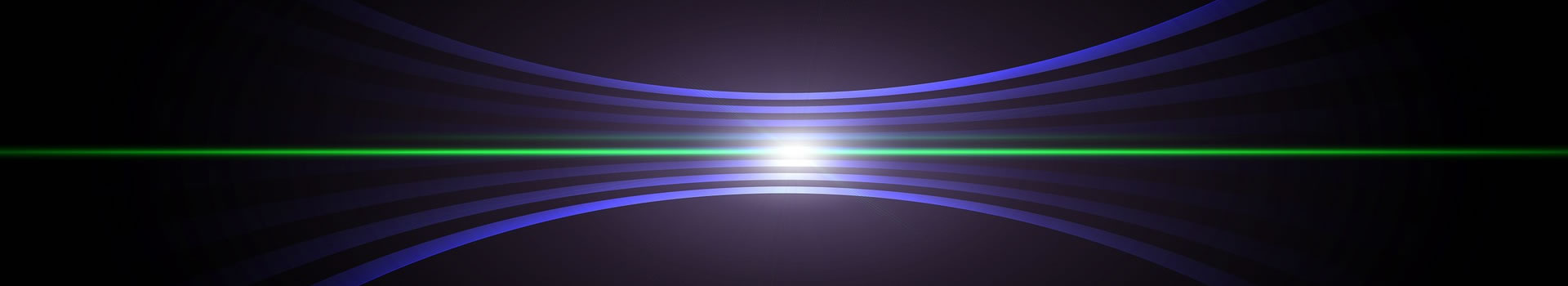

“老九河池预应力钢绞线价格,他认得你。你怎么说?”
座山雕的声音不,像一块冰掉进了炭火盆,滋啦一声,把满屋子的热气都给浇灭了。
空气里那股子酒味、肉味、汗味,好像一下子被冻住了。
几十双眼睛,都跟狼眼睛似的,绿油油地全钉在我身上。
我能感觉到那目光的分量,一斤一两,都压在脖子上。
他没问我,他是在给我递一把铁锹,让我自个儿挖坑,把自己埋了。
威虎山上的雪,埋个人,连个鼓包都看不出来...
01
张乐山还不是座山雕的时候,他是个在山东活不下去的毛头小子。
那年头,地里长不出粮食,人命跟野草一样。风一吹,就倒一大片。
他爹娘没了,里就剩个破草棚。他跟着人流,往关外走。都说关外有活路,黑土地上能刨出金子。
火车是闷罐车,人挤着人,像一罐头快要臭掉的咸鱼。
车轮子哐当哐当,听得人心慌。
张乐山缩在角落里,闻着一股子尿骚味和汗酸味,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窗外。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刮着刀子一样的风。
到了东北,金子没见着,见着的是一望无际的林子和没过膝盖的雪。
他在一个叫石头河子的地方落了脚,给一个木材厂当伐木工。木材厂的老板是个白俄,大胡子,脾气爆,手里总拎着一根皮鞭子。
每天天不亮就得进山。雪地里,哈出的气转眼就结成冰碴子。
锯木头的声音,在空旷的林子里传出老远,听着有点凄凉。
张乐山年纪小,但手脚利索,力气也大。一棵几十年粗的松树,他和另一个壮劳力,半天就能放倒。
木头顺着冰道往下放,喊着号子,声音都喊哑了。
晚上回到工棚,就是一碗苞谷面糊糊,里面见不到几颗米。手上的口子,冻了裂,裂了再冻,跟老树皮一样。
他不多话,干活,吃饭,睡觉。工棚里的人天南地北,喝点烧刀子就开始吹牛,骂老板,想女人。张乐山就听着,眼珠子在黑暗里一动不动。
有一次,发工钱。白俄老板说木头在江上漂走了,这个月工钱减半。
工人们不干了,围着要说法。白俄老板的鞭子就抽下来了,抽在领头的一个汉子背上,一道血印子。
汉子们都蔫了。
张乐山站在人群后面。他看见白俄老板的皮鞭子在空中甩出一个油亮的弧线。他看见那个领头的汉子跪在雪地里,像一条挨了打的狗。
那天晚上,工棚里死一样安静。
过了没几天,白俄老板被人发现死在了自己的木屋里。脑门上一个血窟窿,瞪着眼睛,好像看见了什么吓人的东西。
没人知道是谁干的。管事的报了官,官府的人来看了看,在雪地里踩了一圈脚印子,就走了。这种事,在当时的东北,不算事。
没多久,张乐山就不见了。他带走了厂里好的一杆猎枪,还有几盒子弹。
他进了山,真正的山。
山里的日子,比伐木场还难。吃的得自己找,住的得自己搭。冬天,大雪封山,能把人活活困死。但张乐山活下来了。他好像天生就是山里的人。
他的眼睛,在林子里比鹰还好使。隔着一片林子,他能看见雪地上兔子跑过去留下的一串小脚印。
风雪天,别人看出去白茫茫一片,他能分清远处晃动的是树枝,还是人影。有人说,他的眼睛是阴阳眼,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他的腿也快。在雪地里,他踩着自制的滑雪板,滑得像一阵风。追野猪,撵狍子,没他追不上的。
后来,官兵剿他,他在前面跑,官兵在后面追,追着追着,人就没影了。雪地上,脚印子浅得像猫走过一样。
厉害的,是他的枪。
那杆从木材厂顺出来的老猎枪,在他手里,就跟活了一样。他不怎么练,但枪感好得邪乎。
有一次,他跟另一伙土匪起了冲突。对方十几个人,把他堵在一个山坳里。对方头子隔着几十步远,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喊话,让他把枪放下。
话还没说完,张乐山抬手就是一枪。
子弹不偏不倚,正中对方头子的眉心。那头子晃了一下,直挺挺地就倒下去了。
剩下的人都吓傻了。
张乐山没开二枪。他就那么站着,枪口还冒着青烟。山风吹过,把烟吹散了。
那伙土匪,当场就散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跪下来磕头,喊他大当。
从那天起,张乐山就不是张乐山了。
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叫“座山雕”。
意思是,这片山林,他就是那只蹲在山顶上,俯瞰一切的雕。
02
座山雕的威虎山,不是一天建起来的。
是靠血,一滴一滴浇出来的。
他收编散匪,靠的不是仁义,是狠。不服的,就打。打不过的,就杀。
有个叫“翻天龙”的匪,手下有三十多号人,不把座山描放在眼里。座山雕没带多少人去,就带了七八个心腹。
他没在山下摆开阵势打,那是傻子干的事。
他让人摸清了翻天龙山寨的暗哨,半夜里,几个人像狸猫一样摸了进去。没惊动任何人,直接摸到了翻天龙睡觉的屋子。
翻天龙正搂着抢来的女人睡觉,鼾声打得山响。
座山雕没用枪。他用刀。
二天,翻天龙的手下发现,他们大当的脑袋,被挂在了山寨门口的旗杆上。眼睛还睁着。
山寨里的人,没一个敢动的。座山雕就坐在聚义厅的虎皮椅子上,擦着他那把刀。刀上没有血,擦得很亮。
“从今天起,这山头,归我。”他说。
没人说话。
座山雕的规矩很严,他说的话,就是王法。手下人偷藏了东西,被他知道了,他也不骂。他让人把那人的手,按在桌子上。
他问:“哪只手拿的?”
那人吓得尿了裤子,说不出话。
“不说?那就两只手都别要了。”
座山雕手起刀落。
从此以后,再没人敢背着他搞小动作。
他对外面的人,更狠。
威虎山周围的村子,都得给他交“保费”。交了,他就保你平安。不交,他就让你破人亡。
有个姓王的地主,里有点钱,觉得自己有丁,有炮楼,硬气,不肯交。
座山...雕派人去“请”他。王地主不开门。
当天晚上,王地主的炮楼就着了火。不是从外面烧的,是从里面。没人知道座山雕的人是怎么进去的。
火光冲天,王地主一老小,在里面哭爹喊娘。座山雕就带人坐在不远处的山坡上,烤着火,看着。
他说:“听听,这动静,比过年放炮仗热闹。”
手下的人都跟着笑,笑得让人心里发毛。
王地主烧成了平地。
这事传出去,再没人敢不交钱。交钱的时候,还得磕头,说谢谢雕爷赏饭吃。
座山雕出名的酷刑,叫“点天灯”。
这个刑罚,他轻易不用。只用在让他恨之入骨的人身上。比如,叛徒。
他手下有个叫“小东北”的,机灵,会说话,挺得他喜欢。后来,小东北勾搭上了官府,想把座山雕卖个好价钱。
事情败露了。
座山雕没立刻杀他。他让人把小东北绑在寨子中央的柱子上。然后,他亲自,一层一层地往小东北身上缠布条,从脚踝一直缠到脖子。
缠完了,他拎过来一桶油,也是他亲自,从头到脚,慢慢地浇下去。
油浸透了布条,顺着往下滴,在雪地上印出一个黑乎乎的人形。
小东北已经吓得不成人形,嘴里胡乱地喊着,求饶。
座山雕不理他。他看着天,好像在等什么。
等到天完全黑了,山里起了风。他才划着一根火柴,走到小东北脚边。
他把火柴凑到浸满油的布条上。
火苗“呼”地一下就蹿了起来。
火顺着布条,一圈一圈往上烧。一开始,小东北还在惨叫。那声音,不像人发出来的,像被掐住脖子的野兽。
后来,就没声了。
整个人,成了一个火炬。在黑漆漆的山里,烧得特别亮。
威虎山上所有的土匪,都被命令站在旁边看。有的人吐了,有的人吓得腿软。
座山...雕就站在前面,面无表情。火光映在他的脸上,一明一暗。
他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见,背叛他,是什么下场。
电影里拍的“百鸡宴”,跟这些比起来,就像小孩子过。真实的座山雕,他的残暴,不是为了吃喝,是为了恐惧。他要让所有人的骨头里,都刻上对他的恐惧。
日本人来了。
满洲国成立了。东北的天,换了颜。
很多土匪,都觉得这是个机会。要么投靠日本人,当个“治安军”,吃香喝辣;要么就跟日本人对着干,打出“抗日”的旗号,也能收拢人心。
座山雕哪个都没选。
他的地盘,就是他的国。谁也别想碰。
日本人很快就注意到了盘踞在牡丹江一带的座山雕。这股土匪,神出鬼没,不好对付,影响“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安定。
关东军派了一个叫山田的少佐,带着一个翻译,上山“招抚”。
山田少佐很傲慢。他觉得,对付这种土匪,给点好处,给个官衔,他们就会像狗一样摇着尾巴过来。
他们在威虎山下,按规矩喊话。
座山雕让他们上来了。
聚义厅里,座山雕坐在虎皮椅子上,脚边卧着两条大狼狗。山田少佐走进来,挺着胸膛,腰里的指挥刀锃亮。
翻译官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无非是“皇军”的威严,和“共存共荣”的好处。说只要座山雕归顺,就给他一个“讨伐队”大队长的职位,给枪给钱。
座山雕一直没说话,就在那听着,手里盘着两个铁胆。
等翻译说完了,座山雕才慢悠悠地开口。
“枪,要多少给多少?”
翻译愣了一下,跟山田商量了几句,说:“只要雕爷忠心为皇军力,武器装备,不是问题。”
“钱呢?”
“每月都有大洋。”
“行。”座山雕站起来,“东西什么时候送来?”
山田少佐笑了。他觉得事情办成了。
一个星期后,日本人果然送来了一百多条三八大盖,几万发子弹,还有几箱子大洋。
座山雕的人,敲锣打鼓地把东西迎上山。
当天晚上,威虎山大摆宴席,庆祝“升官发财”。
二天,座山雕就带着人,拿着日本人给的新枪,下山把附近一个亲日的地主给抢了。抢得干干净净。
消息传到山田少佐耳朵里,他气得脸都绿了。他这才明白,自己被这个土匪头子给耍了。
他立刻组织兵力,要“讨伐”座山雕,让他知道大日本皇军的厉害。
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加上一个营的伪军,浩浩荡荡开进了山里。
他们以为,凭借精良的装备和严格的训练,对付一群土匪,是手到擒来。
他们错了。
在林海雪原里,他们的优势,全成了劣势。
山里的路,又窄又滑。他们的军车开不进来,大炮也拉不上来。士兵穿着皮靴,在雪地里一走一个坑,走不了几里路就气喘吁吁。
座山雕的人,穿着自己做的乌拉草鞋,踩着滑雪板,在林子里像猴子一样灵活。
日本人连座山雕的影子都摸不着。
他们刚安营扎寨,准备做饭。林子里“啪”的一声枪响,一个正在烧火的日本兵就倒下了。等他们反应过来,组织火力往林子里扫射,那边早就没人了。
子弹打在树上,噼里啪啦,除了掉下来一堆雪,什么也打不着。
晚上,他们不敢睡死。总觉得四面八方都有眼睛在盯着他们。冷不丁,岗哨就被摸了。人不见了,二天在几里地外的树上,能找到尸体,被冻得邦邦硬。
日本兵被折磨得快疯了。他们看不见敌人,却时时刻刻感觉到敌人的存在。这种恐惧,比真刀真枪地干一场还折磨人。
山田少佐带的队伍,在山里转了半个月,伤亡了三十多人,连威虎山的山门都没看见。后,粮草不济,只能灰溜溜地撤了回去。
这次“讨伐”,成了关东军内部的一个笑话。
座山雕的名声,更响了。他成了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日本人拿他没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不太过分,就不去主动招惹他。
座山雕也不在乎什么民族大义。他打日本人,不是因为他国。是因为日本人动了他的地盘,碍着他发财了。
在他眼里,日本人,官府,还是其他的土匪,没区别。都是他这只山中老雕眼里的猎物,或者,是来抢食的对头。
谁来,他都敢碰一碰。
03
日本投降了。
东北的天,又变了。
穿黄军装的走了,穿灰军装的来了。这支队伍,叫东北民主联军。他们跟以前的官兵不一样,跟日本人也不一样。
他们来了,不只是要剿匪,他们还要扎根。他们发动群众,分田地,建政权。
时间回到1948年11月,此时正是淮海战役开始的时间段,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国民党黄百韬部7兵团被华野大军包围在碾庄一带,而我们的故事也从此时开始。
博时基金的王诗瑶,曾经可是投资圈里响当当的人物,顶着“消费女神”的光环,钢绞线厂家被无数基民寄予厚望。她管理的消费主题基金,在前期也确实有过亮眼的表现,吸引了一大批投资者跟风买入。那时候,大仿佛看到了财富增值的希望,纷纷把钱投了进去,想着跟着“女神”吃肉喝汤。
座山雕这样的土匪,成了他们眼里须拔掉的钉子。不拔掉,老百姓心里就不安,根据地就建不稳。
牡丹江军分区下了死命令,须在冬天,解决威虎山。
任务,交到了侦察排长杨子荣的手上。
杨子荣这个人,跟座山雕有点像。不是说他狠,是说他“野”。他也是穷苦出身,在社会上闯荡过,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他懂江湖上的规矩,会说黑话,脑子活,胆子大得没边。
派他去,再合适不过。
去之前,团里给他准备了好的装备,想给他多派几个人。
杨子荣都不要。他说:“人多了,目标大,反而容易露馅。我一个人去。”
他就穿了一身破皮袄,脸上抹了锅底灰,腰里别着一把盒子炮,看着跟个走投无路的土匪没什么两样。
他没直接上威虎山。他知道座山雕疑心重,直接去,等于送死。
他先去了另一个叫许大马棒的土匪窝。在那混了几天,摸清了道道,然后故意跟人闹翻,带着一张“联络图”跑了出来。
那张图,是真的。是部队之前缴获的,上面有各个匪巢的暗号和路线。
这张图,就是他去威虎山的敲门砖。
他故意在威虎山的地盘上,被座山雕的哨兵抓住。
被带到聚义厅的时候,杨子荣一点不慌。他昂着头,一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厅里坐满了土匪,一个个横眉竖眼,杀气腾腾。正中间那把虎皮椅子上,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瘦,但精神头很足。两只眼睛,跟鹰似的,盯着你的时候,好像能看穿你的心肝脾肺肾。
这就是座山雕。
杨子荣知道,考验开始了。
一个脸上长着痦子的小头目,上来就盘道。
“蘑菇,你哪路来?”(什么人?)
杨子荣嘿嘿一笑,抱拳道:“哈!想啥来啥,想亲娘,来孩儿他娘。”(找同行)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脸怎么红了?”
“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了?”
“防冷,涂的蜡!”
一连串的黑话,杨子荣对答如流,一点磕绊都没有。
厅里的气氛,缓和了一点。土匪们看他的眼神,从敌意,变成了一点好奇。
座山雕还是没说话,就那么看着。
杨子荣把那张联络图掏出来,往桌上一拍。
“雕爷,我胡彪,是从许大马棒那过来的。那孙子不仁义,兄弟我待不下去了。听闻雕爷是东北山头一条好汉,特来投奔。这是我带来的见面礼!”
座山雕的亲信,那个叫“一撮毛”的匪,拿起图看了看,递给了座山雕。
座山雕扫了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这张图,是真的。
但他还是不信。混了一辈子江湖,他信的只有自己。
“你说你是许大马棒那的人,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官府派来的探子?”座山雕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
杨子荣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雕爷,你看看我这样,像官府的人吗?官府的人,有我这么懂规矩的?再说了,我要是探子,敢一个人揣着这宝贝上山?早拿去报功领赏了!”
他说得豪气,在理。
座山雕点点头,没再问。他一挥手,说:“带下去,先当个伙夫,看看情况。”
杨子荣被带到了后厨。他也不恼,该干嘛干嘛。劈柴,烧火,跟其他土匪插科打诨,吹牛喝酒。不出三天,他就跟后厨的人混熟了。他能说会道,出手大方,很快就得了个人缘。
过了几天,座山雕又把他叫了过去。
这次,是在一个靶场。
座山雕指着百步外一根晃来晃去的绳子上,吊着的一个铜钱。
“老胡,听说你枪法不错。打中它,今天你就是我威虎山的兄弟。”
这是二次考验。
杨子荣拿起一支盒子炮,掂了掂。他没急着开枪。他看了看风,又看了看太阳。
然后,他抬手。
“啪!”
一声枪响。
远处吊着铜钱的绳子,断了。铜钱掉在了雪地里。
满场喝彩。
座山雕的脸上,一次露出了笑模样。他走过来,拍了拍杨子荣的肩膀。
“好样的!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威虎山的老九!”
杨子荣成功了。他成了“胡彪”,成了威虎山的九个头领。
他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威虎山的核心机密。他把匪巢的火力点、兵力部署、暗道出口,都一点一点记在心里。
然后,他用土匪之间传递消息的方式,把情报送下了山。
山下的指挥部,根据他的情报,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时间,就定在大年三十的晚上。那天,是威虎山防备松懈的时候。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着。杨子荣在山上,演着他的戏。他跟土匪们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称兄道弟。他表现得比土匪还像土匪,凶悍,粗鲁。
座山雕对他越来越信任。有时候,甚至会跟他聊一些心里话。聊他当年怎么闯关东,怎么杀一个人。
杨子荣就听着,陪着他喝。心里,却在计算着日子。
离除夕,越来越近了。
行动前两天,意外发生了。
那天,一撮毛带人下山“扫荡”,抓回来几个人。其中一个,是个俘虏,以前是另一伙叫“黑风寨”的土匪。
杨子荣当时正在聚义厅里,跟几个头目喝酒。
那俘虏被带进来,跪在地上,浑身发抖。
座山雕坐在主位上,懒洋洋地问:“哪条道上的?”
俘虏哆哆嗦嗦地报了山头。
座山雕“哦”了一声,没什么兴趣。他正要挥手让人拖下去。
突然,那个俘...虏抬起头,看见了坐在旁边的杨子荣。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度惊恐的表情。他像是见了鬼一样,挣扎着,用手指着杨子荣。
“大……大当的!”他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了调,“他!他!他是共军的人!我见过他!他是共军的侦察排长!”
“刷”的一下。
整个聚义厅里,所有的声音都停了。
喝酒的,停了。划拳的,停了。吹牛的,也停了。
几十双眼睛,像是被线牵着一样,齐刷刷地转了过来。
所有土匪的目光,包括座山雕那双鹰隼般锐利、不见底的眼睛,全部聚焦在了杨子荣的身上。
座山雕没有立刻发作,他缓缓地抚摸着椅子扶手上的虎头,嘴角浮现出一丝冰冷的、难以捉摸的笑意,慢悠悠地对杨子荣说:“老九,他认得你。你怎么说?”
04
空气凝固了。
聚义厅里的炭火盆烧得正旺,但杨子荣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一直蹿到天灵盖。
他知道,这是生死关头。一个字说错,他就会被当场打成筛子。
他没有哪怕一秒钟的慌乱。
他的反应,比所有人都快。
没等座山雕的话音完全落下,杨子荣“霍”地一下站了起来。他没有看座山雕,也没有看那个俘虏,而是像一头被激怒的豹子,直接扑了过去。
他一脚,狠狠地踹在那个俘虏的胸口。
那俘虏“嗷”的一声,像个破麻袋一样飞了出去,撞在柱子上,滑了下来。
杨子荣指着地上的俘虏,眼睛瞪得血红,对着座山雕抱拳,声音吼得整个大厅嗡嗡作响。
“雕爷!操他娘的!这小子是黑风寨的!我认得他!”
所有人都愣住了。
杨子荣根本不给任何人思考的时间,他指着俘虏继续吼道:“去年秋天,我们跟黑风寨为了抢一批货,干了一仗!就在夹皮沟!当时,就是这小子,躲在石头后面放黑枪,打伤了我们两个兄弟!我当时一枪,打中了他的大腿!他妈的,没想到他还活着!”
他一边说,一边冲过去,一把揪住那个俘虏的衣领,左右开弓就是两个大嘴巴子。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被我们打跑了,现在又被雕爷的人抓了,看老子在雕爷面前受重用,你就眼红了?想借雕爷的刀,杀我胡彪?你他妈的算盘打得真精啊!”
杨子荣的表演,太真实了。那种被诬陷后的暴怒,那种土匪之间的江湖仇杀,那种粗鄙不堪的咒骂,每一个细节都无懈可击。
他甚至连去年火并的时间、地点、细节都说了出来。这些,都是他之前做功课时,从其他土匪嘴里套出来的。
那个俘虏被打得七荤八素,满嘴是血,本来就吓破了胆,现在更是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呜呜”地摇头。
座山雕一直没说话,他那双鹰眼,在杨子荣和那个俘虏之间来回扫视。
他生多疑,但他的多疑,是基于土匪的逻辑。
一个共军的探子,被当场指认,一反应应该是惊慌,是辩解。
而杨子荣的反应,是暴怒,是攻击,是立刻给对方扣上一顶“江湖仇,栽赃陷害”的帽子。
这太符合土匪的行事风格了。
相比之下,一个来路不明、吓得屁滚尿流的俘虏的话,和一个已经证明了枪法和胆识、并且即将成为自己心腹的“老九”,他更愿意相信谁?
座山...雕的嘴角,那丝冰冷的笑意,慢慢收了回去。
他看了一眼地上的俘虏,淡淡地说:“拖出去,处理了。”
两个土匪上来,像拖死狗一样,把那个还在“呜呜”挣扎的俘虏拖了出去。
很快,外面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
危机,解除了。
杨子荣喘着粗气,脸上还带着“怒气”。他对着座山雕一抱拳:“雕爷,让您见笑了。这狗娘养的,坏了大的酒兴。”
座山雕摆了摆手,重新露出笑容:“没事。江湖上的恩怨,我懂。老九,坐下,继续喝。”
他给杨子荣倒了一大碗酒。
杨子荣端起来,一饮而尽。
酒是热的,但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大年三十,到了。
威虎山上,张灯结彩,跟过年一样。其实,他们就是真在过年。
山下的老百姓,可能连一顿饺子都吃不上。但威虎山的聚义厅里,摆了几十桌酒席。烤全猪,炖野鸡,大盆的肉,大坛的酒。
这就是“百鸡宴”。
天津市瑞通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土匪们一年到头刀口舔血,就盼着这一天。一个个喝得面红耳赤,划拳行令,乌烟瘴气。
座山雕也喝了不少,很兴。他觉得,熬过了日本人,熬过了各路官兵,现在他的威虎山,是铁打的江山。他又得了一个像胡彪这样的猛将,更是如虎添翼。
岗哨上的土匪,也都被叫进来喝酒吃肉了。在他们看来,这冰天雪地的大年夜,谁会来送死?
杨子荣也在喝。他跟这个碰碗,跟那个划拳,比谁都热闹。
酒过三巡,他借口撒尿,走出了聚义厅。
外面,风雪正大。冷风一吹,他浑身的酒意,瞬间就清醒了。
他辨认了一下方向,走到匪巢后山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他从怀里掏出一块红布,绑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插在了雪地里。
这是信号。
做完这一切,他又若无其事地回到了酒席上。
大概半个钟头后。
威虎山下,一支穿着白伪装服的队伍,像幽灵一样,出现在风雪里。
他们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带队的,正是团长。他举着望远镜,看到了雪地里那一点醒目的红。
“行动!”
突击队员们顺着杨子荣之前探明的、防守薄弱的后山小路,悄无声息地摸了上来。
外围的暗哨,早在几天前就被杨子荣以“换防”的名义给调走了。
队伍非常顺利地进入了匪巢。
聚义厅里,还在鬼哭狼嚎。
一个喝醉的土匪,出来解手,刚走到门口,就跟一个白的影子撞了个满怀。
他还没来得及喊出声,嘴就被一只大手捂住了。随即,脖子一凉。他软软地倒了下去。
战斗,就这么打响了。
没有激烈的枪战。突击队员们冲进聚义厅的时候,大部分土匪还在桌子底下找酒喝。
他们看见一群“雪人”冲进来,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冰冷的枪口,已经顶在了他们的脑门上。
“不许动!缴枪不杀!”
酒碗摔在地上,碎了。
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座山雕呢?
他没在聚义厅。他喝得有点多,提前回房了。
杨子荣带着两个战士,一脚踹开了他的房门。
座山雕正躺在炕上,旁边还睡着一个抢来的女人。他被惊醒,一反应就是去摸枕头底下的枪。
一只穿着大头鞋的脚,狠狠地踩住了他的手。
杨子...荣用枪顶着他的头,冷冷地说:“张乐山,别动。”
座山雕抬起头,看清了来人。
不是他的“老九胡彪”。
是穿着一身灰军装,眼神比他还要冷的杨子荣。
他愣住了。他想不明白。他纵横江湖几十年,靠的就是疑心和狠辣,怎么会栽在一个毛头小子手里。
他想了一辈子,也想不明白。
这个曾经让日本人也头疼的硬角,这个在林海雪原上称王称霸几十年的座山雕,就这么被活捉了。
他被抓的时候,身上只穿了一件贴身的白布小褂。
威风了一辈子的枭雄,末路,竟是如此狼狈。
座山雕被押下山,在牡丹江举行了公审大会。
他的罪行,一条一条被念出来。台下的老百姓,有的哭,有的骂。那些曾经被他欺压、破人亡的苦主,用石头砸他。
他一言不发。
枪响了。
张乐山,或者说,座山雕,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他死后,威虎山的那座匪巢,很快就被大雪覆盖了。风吹过空荡荡的聚义厅,发出呜呜的响声,像是在为这个地方的过去唱一挽歌。
黑土地上,延续了上百年的匪患,随着这一声枪响,渐渐走到了尽头。
林海雪原,又恢复了它亘古的宁静。
只是,偶尔还会有老人,在冬天的夜里,对着孩子讲起那个叫“座山雕”的名字。那个名字,像一片阴影河池预应力钢绞线价格,曾经笼罩了这片土地太久太久。而杨子荣的故事,则像一束光,刺破了那片阴影。

 15222026333
15222026333